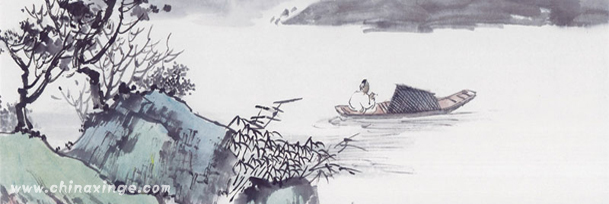当达尔文写《物种起源》一书时,他不能提供任何自然选择来解释进化的好例子。因为当时还没有人能,所以他只有借用一些人工选择的例子,如人工改进牲畜及稼穑,不断选种培育毛最长的绵羊,生蛋多的鸡等等……那时育种者的成就可观,可以改变动物和植物各种特征或特性,甚至使那时的品种与最初的野生品种(Wild Ancestors)之间, 在外表的特征或内在的特性上产生很大的区别。这些区别之大可以达到一个程度,超过了某些生物种与相似种之间的差异。
达尔文使用人工选种为例证其实是引入歧途的一种骗局。改良动、植物的人必须运用他的智慧和专门的知识应人类的需要去选择育种,并且要保护它们不受大自然天择的危害。达尔文学说的精义是想要说明自然界毫无目的(purposeless)随机偶然发生的过程可以代替有智慧的设计(intelligent design)。而他居然使用人为智慧设计者的成就来解释这个论点,这证明了那些愿意无条件接受达尔文学说的听众实在毫无批判的眼光。
人工选种与自然选择基本上不但没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育种的人可以在羊或鸡或鸽子中造成很多自然界没有的变种 (Variations)。他们这样做也存着自然界所没有的目的,包括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看到底生物种研究可以有多少变化,其极限何在。如果育种之目的只希望动物在野外自然环境下生存的话,极端的变异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所有的家禽畜回到大自然后,复杂的变种很快就消失了,下代生存者的外观都回复到原本的野生型态(Wild Type 也翻译成野种或野生型,但是正确翻译应该是"原始型(态)" 或 "先祖型")。由此可见天择过程其实是一种保守性的力量,能防止极端变异的产生; 而人工育种相反地却是在鼓励变异。
人工育种真正的结论显示最高明的育种家也不能超越自然界所设定的极限。物种的变异有人不能跨越固定的规律,所以到目前为止在所有人工培养的动物中并没有产生任何新的物种。所谓新物种,一般公认的定义是指一个新的生物群体与原来的群体产生了生殖上的分野,新群体不能再与原群体交配生出有继续生殖能力的后代。 以狗为例,所有不同的狗都属同一个(生)物种 (Species),因为在生理上来说各种狗都可以杂交生育。虽然有些因体型大小悬殊,不方便交配而不能生育的例外。
法国著名动物学家比埃尔·格拉斯(Pierre Grasse)的结论认为,人工育种的例子是反对达尔文学说的有力证据:
虽然经过千年人为的选种压力,任何不合育种目标的个体都被消灭了,但是始终都没有新物种(New Species)出现。化验比较各种狗的血清、血红素、血蛋白、和受精的可能性都显示,所有不同品种的狗 (Breeds),其实仍然属于同一个物种 (Species)。这项结论是客观测试的结果,不是主观分类学上的意见。事实上,人工选种的结果只不过使狗的基因组(Genome)中去除某些不为人需要的基因,及不同组合的隱性基因显示出来在表现型上,这不能算作创新物种的进化过程。
Darwin on Trial (ISBN 0-8308-1324-1) is a controversial 1991 book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aw professor Phillip E. Johnson.